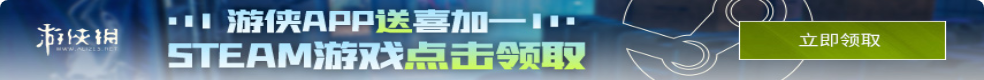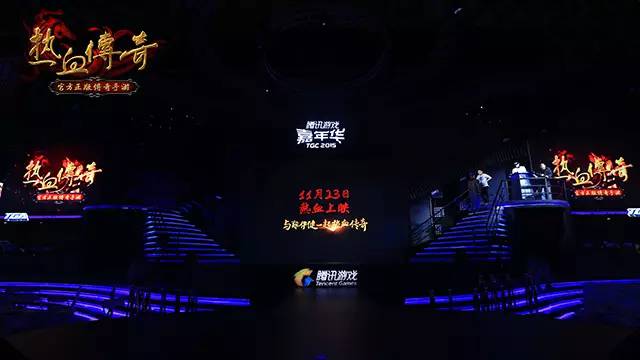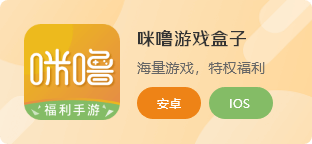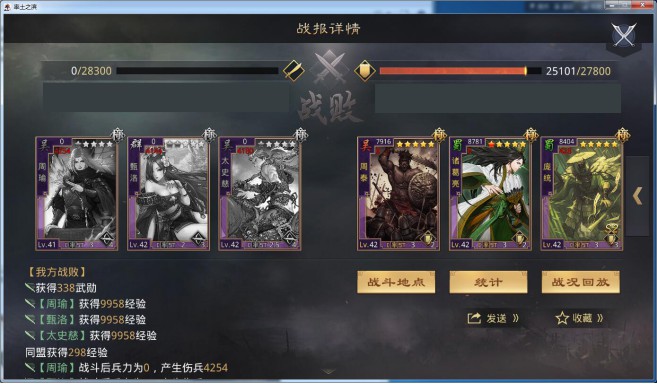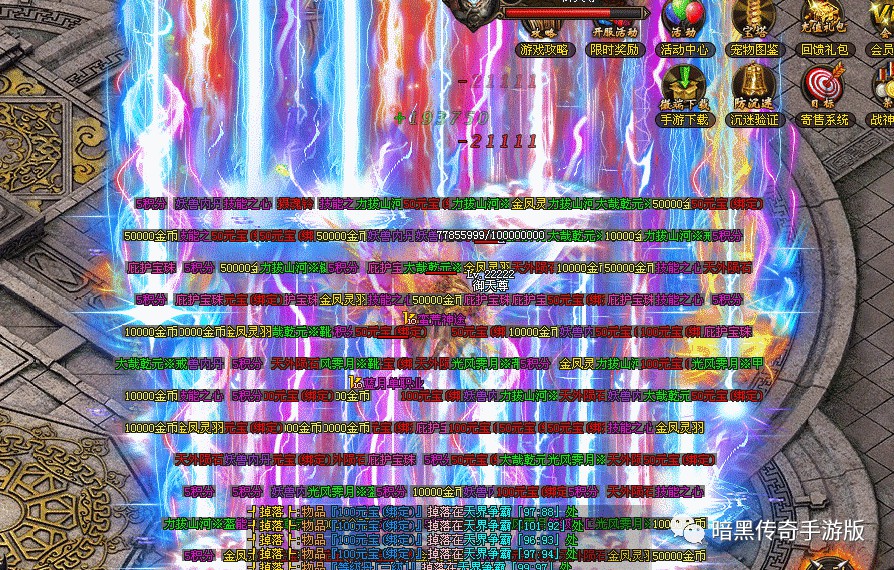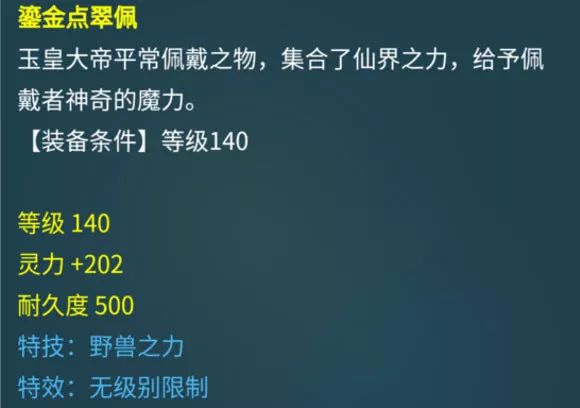11月的梅州,客家围屋的檐角还沾着晨露,的脚步就落在了梅江区西阳镇的田埂上。刚抽穗的晚稻弯着腰,他蹲下来用指尖碰了碰稻穗,抬头问身边的村支书:"今年的谷价稳不稳?村里的电商能把梅菜干卖出去不?"
这已经是党的以来,第N次踏足广东——从2012年深圳莲花山的铜像前,到2018年港珠澳大桥的海风里,从2020年汕头侨批文物馆的老信件旁,再到今天梅州的稻田边,他的每一步都踩在南粤大地的"发展脉络"上,每一眼都望进老百姓的"生活里"。
旁边的张阿公攥着的手,手掌上还沾着刚摘的橘子皮:"您上次说要让客家文化'活'起来,我们村办了山歌培训班,上周孙子还在镇里的比赛拿了奖!"笑着摸了摸孩子的头:"要把客家话守住,把根留住。"
其实的"南粤情",从来都不是"走过场"——2012年在深圳,他盯着高新区企业的研发报表问:"核心技术卡脖子的问题解决了多少?"2018年在珠海,他站在港珠澳大桥上跟工程师聊:"大桥通了,渔民的渔船能顺利出海不?"2020年在汕头,他翻着侨胞的老批信说:"侨胞的权益要护好,他们的乡愁要接住。"今天在梅州,他接过村民递来的客家茶,第一句话是:"老人的养老金按月发了吗?孩子上学要走几里路?"
中午的太阳爬上头顶,走进村里的便民服务中心。办事窗口的小姑娘红着脸递上一杯姜茶:"我爸说,您2018年去珠海时,他就在人群里,您跟他握了手。"笑着说:"那你要帮爸爸记着,今天咱们又见面了。"
有人说,的南粤足迹是"广东发展的时间线"——从深圳的科技创新到珠海的大湾区建设,从汕头的侨乡振兴到梅州的乡村致富,每一次到来都带着"问题清单",每一次离开都留下"解决方案"。但在老百姓心里,这更像"家里人串门"——他记得张阿公的橘子树产量,记得小姑娘爸爸的握手,记得村里的山歌培训班。
傍晚离开时,路边的孩子们举着"好"的牌子喊。风掀起他的衣角,却吹不淡眼里的牵挂——他回头望了眼远处的客家围屋,又望了望田埂上的稻草人,仿佛在说:"下次再来,要看你们的晚稻丰收,要看孩子们的山歌越唱越响。"
党的以来,广东的GDP从5.3万亿涨到13.5万亿,脱贫户的院子里添了新冰箱,大湾区的地铁通到了家门口……这些变化里,藏着多少次深夜改文件的灯光,多少次翻山越岭的汗水,多少次跟老百姓拉家常的热乎气。
暮色里,梅江的水缓缓流着,的身影渐渐远去,但他留下的温度,却像客家娘酒一样,暖着每一个南粤人的心——那是对这片土地的懂,对老百姓的疼,是"每一步都为了让日子更红火"的实在。
就像梅州的老人们说的:"来了,就像自家亲戚,问的都是咱们最操心的事儿。"而这份"操心",正是他对南粤大地最深情的承诺——"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",每一步都算数。